中国人为何总把历史搞错?主张逮捕袁腾飞是胡闹 Warrenchen2010-11-12 00:24:42

中国人为何总把历史搞错?主张逮捕袁腾飞是胡闹(图) 腾讯
深度对话推出“对话历史学家系列”
杨天石:没有进行历史研究之前,我对蒋介石的了解就四个字:人民公敌。但是,用这四个字概括蒋介石的一生,概括他的思想,概括他的历史地位,显然就简单化了。
好像还有人到他的学院去闹,网上有些人主张公安局出来干预,甚至主张逮捕袁腾飞甚至审判袁腾飞。我觉得这个是胡闹。
站在革命史观的角度看问题,就会把许许多多革命之外的东西否定。
人物:杨天石 对话者:张丽萍 编辑:杨余 王憧憧

主张逮捕甚至审判袁腾飞是胡闹
深度对话:你有没有关注最近的袁腾飞事件?网上说袁腾飞被逮捕是因为恶意攻击毛泽东以及社会主义制度,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罪。您个人怎么评价袁腾飞事件?
杨天石:我没有听过他的演讲,也没有看过他的录像,前一段时间闹得很厉害。好像还有人到他的学院去闹,网上有些人主张公安局出来干预,甚至主张逮捕袁腾飞甚至审判袁腾飞。我觉得这个有点胡闹。
本来学术领域应该是一个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园地,应该形成一种辩论的风气、自由争论的风气,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你就要允许存在,不应该因为他的观点你不喜欢,或者触犯了你,你就用行政、法律的办法来对付他,这绝不是正确的指导学术发展的方针。
学术上的分歧只能用学术的办法去解决,这是原则。如果你不同意袁腾飞的观点,你完全可以写文章呀,你也去发表演说、做讲座啊。
深度对话:研究历史和人物,要有同情,才能理解,但不少研究历史人物的学者会比较容易走极端,深陷于同情之中,不能对研究对象持一种客观的态度。但您对毛泽东和蒋介石的研究和作品是很客观的,您是怎么把握这种分寸的?
杨天石:我觉得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最危险的是过分同情他要研究的这个历史人物。研究历史应该是尽量做到最大的客观,绝对不能够掺杂任何个人的感情。人当然都是有感情的,都有喜怒哀乐,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讨厌什么,憎恶什么,这是人所不可避免的,但是研究历史的时候千万要超脱个人的感情色彩。
《礼记》里讲:“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若憎而不知其善,则为善者必惧。爱而不知其恶,则为恶者实繁。”这是我很赞成的:爱之不增其善,憎之不益其恶。不能因为你喜欢他,就增加他的好,不能因为你不喜欢他,就增加他的坏,这是不能够、不应该的,也就是说写历史、写历史人物,如果你把个人感情、个人喜恶掺进去以后,很难保证客观性、科学性与公正性。
所以历史学最重要的就是要实事求是,三分不能说成四分,也不能说成两分,这都是历史学的大忌。

蒋介石不再是人民公敌
深度对话:您是1960年北大中文系毕业的,以前也研究文学史、哲学,后来为什么会转而研究历史呢?
杨天石:这是一个说来话长的题目,详细讲可能两个小时也不够,简单讲就是五个字:命运的安排。
深度对话:您研究近现代史这么多年,心境是否有一个变化历程?
杨天石:我觉得没有什么变化,从我开始研究民国史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我最近出了一本书是我17年前,也就是1993年出的《寻求历史的谜底——近代中国的政治与人物》的再版。在再版的这本书末尾,我有一段话:本书是我踏上近代史研究之途的第一个脚印,但它代表了我的学术追求。
十多年了,初衷未变,追求未变,风格也未变。是也、非也,恭候指教。当年这本书是我多年论文集合,最早的一篇文章是上个世纪60年代写的,所以从我踏入近代史研究领域,一直到现在,初衷未变,追求未变,风格也未变。
深度对话:您赶上了三次大的社会政治变动。一次是“新中国”成立,一次是“文革”,再一次就是改革开放。这些对您研究近代史有什么影响吗?
杨天石:解放前后的历次运动我差不多都经历了,要说这些运动对我的帮助,简单说就是一点:让我看问题不再简单化。我在大学念书的时候曾经有一个想法——要掌握事物的全部复杂性。你要了解整个世界,了解一个人,要注意掌握它(他)的全部复杂性。
所谓“掌握全部复杂性”,就是看问题不要简单化,不能“一点论”。这是从历史运动里面所得到的一个教训。研究历史也是这样,绝对不能简单化,不能“一点论”,而应该努力地掌握历史的全部复杂性。
咱们拿人物来举个例子。没有进行历史研究之前,我对蒋介石的了解就四个字:人民公敌。但是,用这四个字概括蒋介石的一生,概括他的思想,概括他的历史地位,显然就简单化了。毛泽东也批评过对人物和事件的简单化,过去研究“五四运动”,好就是绝对的好,坏就是绝对的坏。
毛泽东批评这种绝对好、绝对坏的观点是“形而上学”。但这常常就是我们过去对历史人物的看法,历史研究过程中这种“形而上学”的地方俯拾即是,实在太多了,你低下头来捡一捡哪儿都是。
重新审视“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
深度对话:您认为在评价中国历史上的人和事的时候有没有一个标准或者是一个参照系?如何才能做到尽可能不带偏见地去看人看事,不带偏见地以一种同情的心态去看待历史和历史人物呢?
杨天石:这个标准,可以借用和参照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作为研究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可以叫“三个标准”。
比如,第一条,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我们完全可以借用来评价一个历史人物,看他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还是向后倒退。第二条,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要求,看他对于文化发展是推向更高的层次,还是阻碍文化的发展。第三条,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研究一个历史人物要看他对民族、对于老百姓、对于人民是有利还是无利。
深度对话:史观问题在近现代史学界尚未争出胜负,您对革命史观、现代化史观和人文史观怎么看?
杨天石:这个问题牵涉到中国近代史应该怎么写的问题,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革命史的,一种是现代化的。我个人不大赞成这种模式划分。
革命化的模式有它的毛病:容易突出革命,忽视社会的方方面面。拿近代史来说,过去通常讲近代史有三次革命高潮,就是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用“三个代表”来分析的话,恐怕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都不能做很高的肯定,你能说代表先进生产力吗?恐怕不能算。你说它代表先进文化吗?恐怕也不能算。
义和团不仅不代表先进文化,代表的反而是一种落后的、狭隘的旧文化。
如果把一部近代史看成刚才讲的三大高潮,那么三大高潮中的两大高潮都站不住脚,都无法肯定。站在革命史观的角度看问题,就会把许许多多革命之外的东西否定。
比如“洋务运动”,我们很长一段时间是否定的,为什么否定呢?八个字:对外投降、对内镇压。就是因为洋务派对外签了好多“卖国条约”,包括曾国藩、李鸿章,对外是妥协的、投降的,对内镇压太平天国。
但是,用刚才讲的“三个标准”去衡量:第一,“洋务运动”从国外引进了先进生产力,中国原来是农业社会,现在把西方的现代工业,包括军事工业引进来,它当然会推动中国历史的发展;第二,“洋务运动”办学堂、培养翻译人才、送中国的学生出国留学,学了声光化电,声学、光学、化学、电学,这都推动了先进文化嘛。
所以,如果我们用三个标准来衡量的话,“洋务运动”就不能全盘否定,它是代表中国近代社会向上发展的一个环节、一个阶梯,就要肯定它在中国历史上的积极正面的作用。
虽然洋务派不赞成革命,甚至也不赞成改革,不赞成维新,但它毕竟是中国现代社会向前发展的一个阶梯,这个阶梯你要跨过去是不可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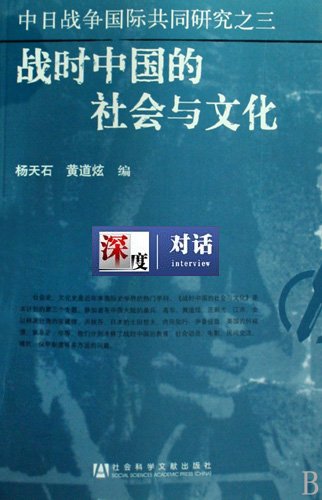
所以,我觉得革命史的模式会把有些不该肯定的东西肯定了,把该肯定的忽略了。把义和团运动作为革命高潮,那是荒唐透顶。义和团的口号“扶清灭洋”,“灭洋”,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当然要反对,“扶清”的革命性何在?说句老实话,我一点也看不到。
所以,我觉得按照所谓的“革命史观”,可能是肯定了不应该肯定的东西,否定了不应该否定的东西。
另外,革命史的模式会把近代史的丰富性排除。比如近代史上曾经盛行的两种思潮,一种叫“科学救国”,一种叫“教育救国”,一部分人希望通过发展科学救中国,一部分人希望通过发展教育来救中国。
按照革命史的模式,只有革命才是正确的,所以科学救国、教育救国都被认为是一种改良主义的思潮,常常被否定。
所以,我不赞成所谓“革命史”的模式。现代化的模式是不是更好一点?更全面一点?我没有想好,我个人主张写历史不需要什么模式。先确定一个模式,很可能会画地为牢,就把自己局限住了,或者说把自己困住了。
如果说非要有模式,那就只有一个模式,就是实事求是的模式,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写,历史原来是什么样的你就怎么写。
这牵扯到“方法论”的问题,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讲过一段话:“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段话不太好懂,核心意思是原则是从历史里抽象出来的,所以不是历史去适应原则,而是只有原则符合历史的时候,这个原则才是正确的。
人们在写作之前可能要给自己规定几个这样那样的原则,所谓“革命史”模式也好,“现代化”模式也好,实际上都是人们确定的原则,就是写历史的指导思想。
我觉得坚持一个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一个还原历史本来面目的原则,这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