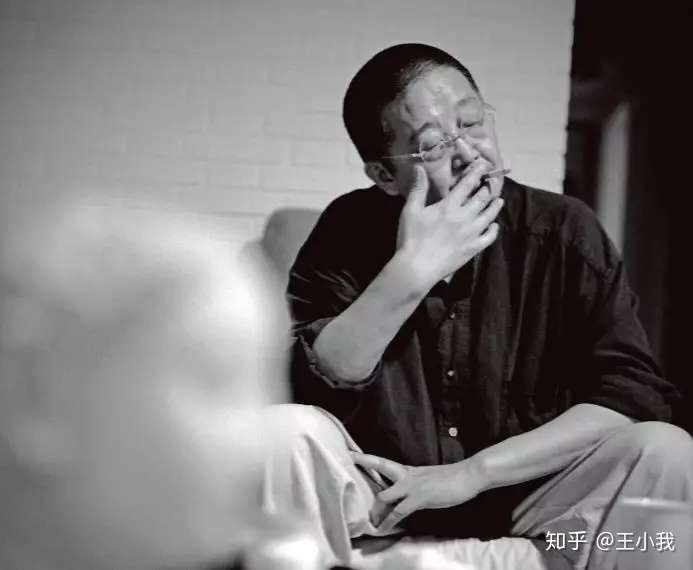阿城,中国电影界的扫地僧 (6) 上善若水_19962020-11-06 00:18:50
作者:王小我
06.看电影不是我们的生活方式
阿城贪吃。作家陈村说,阿城吃饭才叫吃饭:
一桌的菜,花里胡哨的那些不大去夹,喜欢的是猪大肠一类有质感的,按他老人家的期待,不要洗得太干净。他也喜欢红烧肉之类结结实实的食物。吃两块肉,浇点肉汁在米饭上,食不语,目不斜视地吃得干干净净,请跑堂添饭,再吃干净。放下碗筷,抹抹嘴,点上烟,开始说话。其他人可以边吃边跟他聊天,他再不碰食物。
莫言和他一起去大连开过一个笔会,亲见过饭桌上的阿城,动起筷子,亲儿子不认:
那就是吃起饭来不抬头也不说话,眼睛只盯着桌子上的菜盘子,吃的速度极快,连儿子都不顾,只顾自己吃。我们还没吃个半饱,他已经吃完了。
有一次,侯孝贤托人带到北京一盒牛肉干。儿子拿了几大块到大街上与邻居小孩分吃。吃完了回来再要,阿城急了,说,告诉他们,你爸爸也喜欢吃。
阿城祖籍四川,口重,好川菜。他判定川菜馆好不好吃,有绝招。
一次阿城的编辑杨葵跟他去一家川菜馆,落座半天,阿城翻来覆去看菜单,不点菜。服务员站一旁快不耐烦的时候,他开口了:鱼香肉丝吧。人家还等他继续,菜单已经合上了。服务员一走,他透了底:这家玄,挑个最简单的菜,做做试试,不好换一家儿。
阿城平时行踪隐蔽,轻易不进城,有肉例外。导演刘奋斗和他密切往来过一段时间,摸清了阿城脾性。只要说请他吃肉,“一忽悠,他就进城了。”
不下馆子的时候,阿城爱吃面。朋友去他家,要么见他热气腾腾一碗面端在手上,眼镜上的水汽也顾不上擦,呼噜噜吃起来。要么见他手上拖着一斤面,洒脱地回家来。
他招待客人也是吃面。煮上一锅切面,丢进半颗白菜,旋即找来半碗肉末儿炸酱拌进面里,一人一大碗。
吃之外,阿城也能喝。诗人芒克随他下海经商那阵子,见过阿城的豪饮:事儿还没谈呢便先开吃开喝。阿城当时的酒量大得惊人,他把一整瓶老白干全倒进一个大缸子里,菜没吃一口酒已喝完了。
喝酒也出过洋相。有一回在杭州开会吃饭,用的是黄酒。阿城有点兴奋,频频与人干杯。陈村也在场,问他喝没喝过这种东西,阿城说没有,像汽水一样,好喝。黄酒性子慢,但阿城喝的急,一杯一杯下去,越喝越飘,最后是被众人抬上楼,抛在床上。陈村说,那天之后,我再没见阿老喝酒,他抽烟照旧。
到后来,歌手苏小明组了个“吃喝委员会”,成员有阿城、姜文、王朔、洪晃、田壮壮等。
有一次,苏小明和阿城、郑晓龙、刘索拉几个人去姜文工作室找他玩,来前,姜文说,我给你们做饭,想吃什么。苏小明说,简单点就行。到了后,姜文导游一样领着一行人绕天安门转了两圈,回来桌上一锅面,一碗炸酱,一盘煮黄豆,一盘白菜。几个人看傻了,说你这也太简单了。姜文说,不是你让简单点吗?阿城泰然不语,吃两口,说,劳驾递两粒黄豆给我,我怕一站起来又得吃一碗。
大家爱往阿城身边凑,但也都承认,阿城不好相处,经常一句话把人噎住。住在洛杉矶时,有一回他请诗人芒克吃日本料理,另外还请了几个朋友和女士。他一见芒克,说,你瞧我胖了吧?你再瞧这些女人的奶子。美国这地方就是养人。看把她们吃的!个个奶头都立直了,像朝天椒似的。说完旁若无人,照吃不误。

九十年代末,杨葵有一次送阿城回酒店路上,问,晚上要不要一块儿吃饭,我跟他们说了你来北京,他们都特别想见你。阿城坐在车上,望着窗外,自言自语一句,一个人想自己呆会儿,还真不容易。杨葵一阵尴尬。
杨葵研究过阿城为什么不好接触:从知青时候,甚至从小时候,他就不能直抒胸臆,总是要防范一些东西。因为家庭出身。除去这一层,这其实是一种修养。我给总结叫“能一个人呆得住”。能不能面对寂寞,说得更直白一点,是能不能面对无聊。
在阿城看来,当代人的绝境,就是无聊:
咱们这个时代我也是非常喜欢,但是这个时代的绝境是无聊。并不是说你要找一个血淋淋才叫绝境,你怎么能够穿越这个绝境,你有这个能量、有这个智慧、有这个经验吗?没有。
即便无聊不是每个人的绝境,但他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绝境。
他去意大利一所大学开讲座,引荐的教授说,我看过阿城的小说,真想过那样的生活。阿城当场打断,说,人生不是这样,不是因为你穷就必然产生什么。人生是任何人都会有绝境的,穷人会有,身价百亿者也有,在绝境面前,人是平等的。
说完,当时阶梯教室里有几个意大利学生就哭了。阿城知道他们在哭什么:我猜是有钱人家的孩子,因为一般人不认为富人也会有心理绝境。
2019年,阿城70岁。极少露面。
2009年起,中央美术学院造型学院聘他做客座讲师,他给研究生讲造型史和色彩。每学期讲五个星期,每次晚饭后开课,没有讲义。

十年讲下来,整理为《洛书河图:文明的造型探源》和《昙曜五窟:文明的造型探源》两部书。陈村看了《洛书河图》,说,文气甚为凶猛。
这两部书,多图,少字。有人评论说,长于造型间的勾连对比,短于实证。阿城觉得这是外行话:
讲造型,造型之间的勾连对比比文字解释要直接而强有力,一般人对文字比较关心,对图像的辩识能力则差很多。你如果和一个画家走过同一条街,你一定比画家少看到很多东西。
讲课之余,关起门,他读书写作,持续到早晨,上午休息。阿城的主要文学作品,都出版于2000年前。近些年,版本常新,文学新著,没再出。
问起他为什么不写东西,他大叫冤枉:写啊,一直在写啊。他很早开始用电脑写作,且同时开工多个作品:
我的写作习惯是,写到一个地方,有了新的想法,就将在写东西编一个号码,把它 save 起来,另开一个新档,按新的想法写下去。再碰到新的想法时,再 save 起来,再开新档。所以电脑里头大概有三千多个这种档案号码。
侯孝贤说,据说里面有百万字,都是他当年下乡的故事,但后来电脑出了点状况,这批稿子全没了。
又问,怎么不发表?他有几个说法。
一是,没有形成发表习惯。他觉得,写作就像看书,不一定要发表、给人看,不太有目的性。偶有新作,他大部分发表到国外刊物上,让人翻成自己也看不懂的外文。
二是,他将私人写作视为一种漫长的风格练习:把一件事情,一种风格写到极致,是你个人的事,必须不断地自己探索。“现在人学人家长处地耐心有时也没有,常常看到一点皮毛,就觉得自己全明白了。”
第三个说法,才算暴露他不发表作品的真正缘由:从出版来说,中文阅读界不幸还相当保守,有些领域不如古人,或不如外国。有些东西发表在意大利、日本、法国没问题,发给大陆、台湾一定有问题。“隐私的东西公开,常常会毛烦人,就好像客人来了,你忘了收起晾着的内裤。”
追究起来,他认为这跟意识形态有关系,“我们民族有个意识形态,比如说世界杯踢进去了,大家都是 ‘我们终于踢进去了!’这个劲儿,如果这时候你写一个说,’这个事情没有什么’,那全国人民跟你过不去。”
宁财神是阿城的书粉,《闲话闲说》熟到能背下来。阿城说,什么时候我送你一本。你现在看到的国内的版本是有些删节的,删节了三分之一。
电影,依然是他生活中的一部分。
不参与电影制作的时候,他给人帮忙。2003年,刘奋斗弄完《绿帽子》剧本,拿给阿城看,想请他来当监制。阿城一挥手:你觉得用我的名字能帮到你,就用。后来刘奋斗又问能不能帮忙联系焦雄屏做制片人,阿城马上就打电话。
他也去做电影节评委。2005年,他受邀成为当年威尼斯电影节唯一一位华人评委,主竞赛单元评审环节,阿城与其他几位评委舌战4小时,力护李安,最终李安凭《断背山》摘得最高奖金狮奖。

他一直关注国内电影和电影市场。?一眼当下中国电影,他一个总的感受是,失望。“每年都会做一些电影的事,谈剧本啊什么的,谈来谈去大家都在谈场面怎么拍或者是谈故事的扣儿,都不进入人。一听这个你就知道还不及格嘛! ”
他把脉两岸三地:大陆电影现在基本上是破产的状态;台湾基本没有电影;香港则是青黄不接。
偶有国产电影爆款,他还是看不到什么希望:像冯小刚、宁浩这样的导演应该多,而不是一两个。多了以后这样的影片才有可能慢慢让观众回到影院,让看电影成为大家的生活方式之一。光靠大片形不成这个。
阿城感慨道,现在看电影已经不是我们的生活方式。他在美国居留多年, 一部新片上映大家都会排着队去看,“如果你周末没看一部电影可能周一上班的时候就被 ‘开除’了。”
现在看大片,成了一道奇观:大片成为事件,就像出了一个事大家要去看现场,好比一个人要从10楼往下跳,大家都跑过去看,从电影院出来都是看完现场以后的反应。
他不凑大片的热闹,宁愿等 DVD:我不愿意进电影院,设备太差,成本太高了,怎么可以一张电影票是吃一顿大餐的钱?太过分了!60块钱一个人吃不完还可以打包啊!不可以这样。这种消费水平绝对是破坏生活方式的。
而整个电影市场,更是跑错了赛道:学韩国、学美国都不对,应该学印度。“就是拍给本国老百姓看,就是歌舞片。不管什么样的人都会到电影院去看,如醉如痴。”
他认为倒退有时也是进步:也许中国大陆需要的是将电影文化恢复到一九四九以前。首先满足本土,国际反而其次。
令阿城对中国电影和电影市场感到失望的因素,当然还有审查制度。他曾向父亲钟惦棐请教,何以每年总有几部影片出麻烦。父亲说,电影是唯一能进中南海的艺术,唯其能进,所以麻烦。
阿城抚今追昔,叹道:大陆曾经是拍电影的乐园,不必担心票房,花钱少的大场面,众多训练有素的演员,触及政治就像床戏一样有吸引力,于是我从艺术方面怀疑许多人因此而懒惰。
家家都有要认真念的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