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与国家 英二2022-05-14 03:35:52
大众与国家
“大众”与国家关系的定位,一方面,“大众”是国家的积极的构建者,另一方面,“大众又作为社会批判的肯定性力量始终在发挥作用。对于现代性来说,由于社会的生产关系存在不平等的一面,“大众” 索求自身利益的斗争,在本质上,是一种生命政治斗争,“代表了解放哲学的标准域”。
“大众” 与国家的对立形式,在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民众使用的是一种 “抵抗的权利” (ius resistentiae)。这种权力声称,一个个体,一个地方的共同体,一个手工业行会有抵制中央的特权 (prerogatives)。作为一种积极的特权(positive prerogatives),它构成了一种有效的,有形的,对可能发生的社会变更的防卫,比如出现在雇佣劳动斗争中的防卫。维尔诺(Paolo. Virno)对它的描述最具暗示性: “它不同于经典的公民的不服从,它不质疑具体的法律,而根本就是对国家的控制发起质疑” 。它是一种通过 “一种无限的抵抗权利” 来行使自我保护。 “抵抗的权利” 与颠覆理论无关,但也常常构成了是合法,还是非法的凸点。
从大众的角度看,社会关系的核心并不是在于个人与国家之间,而是在于大众与国家之间。这也关系到人权与民权概念的差异,现代体制炫耀人权而忽视民权,是一种故意操作,国家的决断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先发制人的攻势,其主要的目标就是堵住大众的表达。
对于现代性来说,“大众”的主要“对象”(其实是“对手”),体现的是与国家的对立。假设硬要套用社会金字塔的比喻来说,大众的 “对手” 是组织并控管塔型结构的 “决定者”。
如何来理解这样的观念? 萱野稔人(Kayano Toshihito)在他的《国家是什么》(國家とはなにか2005)中,就是力图纠正 “国家即为虚构” 抑或 “国家即为话语” 的理论谬误,表明现代国家的特质是来自于暴力的组织化,垄断化,而且,为资本所有制所限定。这也就是说,“国家”(State)是一个“阶级局面” (state of class),它将人民整体加以组织化,并划分为阶级,从而加以生命与政治的控管。在某种意义上,“国家代表阶级利益” 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仍然成立。就它的现代内涵而言,两者确实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资本依附于市场,但市场的本身并不能解释社会的生产关系。凡是市场均有组织,而调节并管理这个组织就是国家。即使是,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国家有衰微的趋势,但并不代表 “国家” 这种组织架构会消亡,至多,只是 “国家” 形式的蜕变而已。毕得(Jacques Bidet)就认为,对“世界” 与 “国家” 应做出区分:世界所代表的是国家跟国家之间的竞争场域,即地缘政治,毕得称之为 “系统面” ;国家则代表阶级斗争的场域,即社会政治,毕得称之为 “结构面” 。在如今的全球化时代,国家 “升级” 到了世界层次,也因此,昔日被区分的系统面与结构面会交织在一起,因此,全球的阶级问题会走向前台。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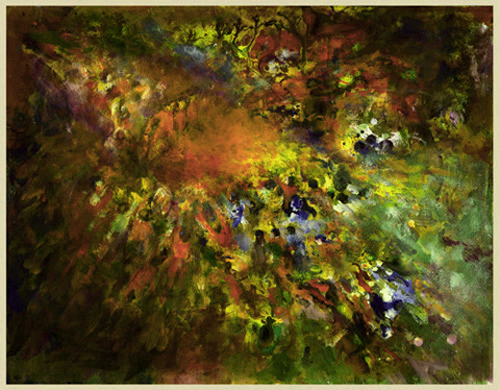 my painting
my painting
.